1 墨西哥人都不用上班吗
飞机起飞,舷窗外是过去四天三夜的游览的墨西哥城,渐渐随着飞机的爬升变成星罗棋布的灯火,好大、好美。
来墨西哥之前的印象就是这里很乱,来了之后发现,除了街头时不时响起的警笛,似乎也并没有之前刻板印象里的那样恶劣。我们住在被戏称为“墨西哥武康路”的罗马区,落地的那天我打车前往民宿与大家汇合,我感叹“空气中都飘荡着塔可的味道”。
来之前以为这地方穷凶极恶、叫人防不胜防;来之前以为这地方会拥堵不堪、以为这座城里的人们会拖沓无为。没想到的是,打车软件上预测的到达时间相当准确,沿路看到的人们也并无半点凶相苦相,而这些刻板印象也在随后的旅途中被一一推翻,我不禁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让我对一座城市下如此定义。也许旅行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在前期准备和身临其境的过程中,不断地建立stereotype,反思stereotype,打破stereotype亦或验证自己的stereotype。它就是一个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待惯了的人,跑到别人生活的地方住上几天又离开的过程。然后我们经历过的每一个瞬间都会在我们身上烙上一些印记。
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里,我已经在群里说“我已经爱上这里了”,也许是因为随处可见的蓝花楹和三角梅,还有和上一站夏威夷(或者洛杉矶机场)对比起来的烟火气。也许只是因为便宜的物价。我们订的民宿就在一颗特别大的蓝花楹树底下,我进门不到五分钟,刚上楼放下书包,窗外便传来了萨克斯声。我探头往外看,想录视频又怕被他发现,只能在这样淡淡的“偷感”里欣赏完这支曲子,旋律听上去很像中国的那首 “是谁 在敲打我窗”。
这种感觉很奇妙,因为你并不知道他在这样的一个周一下午,到别人家门口吹这样一支曲子是为了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心想,“这就是墨西哥人吗?好奇妙!”
然后是,“不对啊,他们不用上班吗?”
2 信息的载体 与遗忘
墨西哥人不上班的似乎不少。爱音乐的似乎也不少。等我们第三天到了距离墨西哥城两小时车程的小城普埃布拉(Puebla),又是被用音乐迎接——我们在一堆蓝蓝的房子面前下了车,一边找着民宿的入口,一边听到一位老先生在街角拉提琴。第二天我们走的时候,他也出现了,只不过这次换成了小萨克斯。我们对他笑笑,他也对我们笑笑。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准备睡觉的时候,又是民宿的窗外,一群青年人在我们窗外的正楼下,唱着我听不懂的西语歌,很动听。他们唱了大概有三五十分钟。在这座城市,好像音乐已经成了一种不足为奇的背景乐。
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就是目标导向的,想知道他们就这样在街头站着弹弹唱唱是为了什么,因为我没在他们的面前见到一部架起来直播的手机镜头,乐器盒子里也不知道一天能收到多少小费,反正我路过的几次都并没有看到有人给。我猜,也许他们就是喜欢音乐吧,也许所谓的目的就是演奏。音乐没有目的,音乐本身就是目的。
在墨西哥,也许是因为和朋友们呆在一起的缘故,最开始我甚至很少拿出手机拍照,这就导致虽然蓝花楹作为市花遍地都有,可我的手机里竟然拿不出一张看得过去的照片。同样的还有一种松树,我称之为“帽子树”,因为在风吹下树的尖会摇摆,很像我想象中魔法师的帽子尖。墨西哥很美,但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机却拍不出来。于是,这样的美,带着热烈的阳光,就这样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墨西哥也成为了一个我下决心以后还会再来的地方。四天有些短暂了。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习惯在每一个美丽或温馨的瞬间掏出手机,也许是为了分享,也许是因为怕自己忘记。直到有一次,我和K在开车回城的路上,高速上的灯光和车里CD播放着《沙龙》,很美。我和K说我想拿出手机录一个视频,K说当然可以,但他不会录,因为要把这样的片段记在脑子里。我才发现,我会害怕有天我把一些美好的时刻都忘了,所以我选择信赖科技和云端胜过信赖大脑;我也不喜欢删聊天记录,我试图保留一切,我想把写过的字和说过的话都记录下来。
而在墨西哥的阳光下,和两位第一次见面的朋友一起走在充满欧陆风情的街道的时候,我竟然第一次懂得了“用眼睛记住就够了”的道理。虽然我不知道K对于那段记忆的脑容量会有多持久,但我开始偶尔回想一些以前旅途和生活中那些未被数码相机记录的时刻。也许现在能想起来的都是值得留下的,而现在想不起来的,都会消失在时间的流逝中——就像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脑海中闪过的每一个念头;就像我们本身。
我开始思考信息和载体。写字的载体是纸张、声音的载体是录音(比如播客)、聊天记录的载体是云端的一串编码、图像的载体是视频和照片;而有些东西也许会有另一种载体,比如声音的另一种载体可能是与你对话的人的记忆,图像的另一种载体可能是与你一起分享这幅景象的人的记忆……所以有些信息的载体也有可能是这些无形的地方,而当某天一起共享这些记忆的人把某个信息全都忘掉的时候,这些信息也就随之消失了,就像我们把信纸烧了、云端存储空间突然崩盘了一样。
这令我突然想起《寻梦环游记》里那句——“真正的死亡是被遗忘”,我好像现在才有了些更深的理解。说来也巧,当时补这部电影其实是在计划墨西哥的旅行,电影的设定是在距离墨西哥城五小时大巴的小城瓜纳华托,五彩的房子高低错落,在亡灵节的时候尤为热闹。墨西哥人传说亡灵节是去世的朋友亲人们会回来的日子,但是只有当还有活人在家里摆放着你的照片的时候,你才能在那一晚“穿过连接两个世界的桥,回到家人的身边”。也就是说,如果某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记得你了,你也就真正的离开了。
在墨西哥城的时候我们参观了著名的人类学博物馆,展馆从人类进化、美洲早期历史、讲到墨西哥历史上各个部落和地区的文化历史,几乎是墨西哥城的必打卡地之一。我们三个在展馆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一边闲聊。也许是前几站的新加坡、东京、夏威夷(包括之前生活的香港)都以近现代文明和享受自然为主,当我来到历史博物馆,看着展出的几百甚至上千年前人类用过的器具、写过的书信、触碰过的墙垣,一下子把我拉出神来。几千年来那么多人类(甚至早期人类)存在过、吃过、喝过、拉过、撒过、说话过、爱恨过、思考过、遗忘过;最终不还是完全消散不见,绝大部分人过三百年都不会被人记得你姓甚名谁,除了极少数人会被后世的某一些人所听闻:文武巨匠、帝王将相,少则几百年,多则几千年。可他们早已入土长眠,幻化成不知道哪一粒沙,从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开始,自己在后世的reputation就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除非它影响到你生前爱的人,或是你的“后代”(如果你在乎的话);可这些人再过个几百年也差不多结束了。即使是“生前有所成就”如埃及法老、秦始皇,毕生为了死后的永生而造地下宫殿、选奢华的陪葬,可他们如果知道自己被挖出来展览在博物馆里,又会怎么想?
同行的两位朋友都是极致利他主义之人,我们一致认为建功伟业这半天,中间屠戮委屈这么多百姓圣灵实在不可取;
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是秦始皇或者法老王,也许我能让几千年后的人学习参观到几千年前的工艺,也许对我来说是有一些意义(but again,我只能抱着这样美好的幻想而死去,而如果不相信死后有来世,其实一切都无从印证)
以及,我好像忽略了大多数人更看重的那种“功绩”:王侯将相对后世有着开创一些制度的意义;思想家的书籍著作可以给后世的人一些启发(but again,我只能抱着这样美好的幻想而死去,而如果不相信死后有来世,其实一切都无从印证)
也许,关于死亡,关于人生的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自洽就可以了。对于我来说,似乎就是过好每一天,尽量开心。但如果我相信佛说的众生皆苦,好像不开心也没关系。也许人生的意义就是在活着的时候活着。以及,在死去的那一刻死去。
3 刻板印象
其实普埃布拉并不是一座小城,而是墨西哥第四大城市,Puebla省的省会,又有重要历史和经济意义(我原以为这里对标中国的上海,问了Deepseek发现其实类似于南京或西安);只不过这里的发达程度和人们生活方式,对于来自“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我们来说,好像一个小镇。
动笔这篇文章是在前往普埃布拉的路上,当时同行的朋友Arena坐在前排看书,是港大教授写的关于王家卫的电影;打车的司机掏钱准备交高速费,一不小心按成了摇下后排的车窗。
过了收费站,眼前出现了一栋很高的建筑。也许是因为它在这海拔两千七百米的干燥高原中确实显得有些赛博突兀,Arena也忍不住用西语问了司机。她们简单地问答着,我就在后排默默地听着,因为我知道几秒钟之后,Arena一定会转过头来告诉我刚刚的对话说了些什么。这是墨西哥之旅的第三天,也是从独自旅行转换成多人旅行。出发前我发现Arena既会西语又很靠谱,便悄悄地几乎没做攻略。好在大家都是轻松随意的人,也纵容我睡着不知道在哪个时区的懒觉,我竟然真的只要无脑跟随+坐等群收款就好了,岂不美哉!
在墨西哥城的时候,F说很想问司机觉得中国人和墨西哥人长得像不像,Arena便作翻译了。司机说,挺像的,他们都觉得中国人很好看,只不过中国人的皮肤白一点,墨西哥人的眼睛大一点。我们听到最后这句的时候都“炸“了,不能说是一种歧视,只能说全地球对亚洲人刻板印象再次得到了印证。随后我们的整个对话中时不时地蹦出“眼睛大”相关的评论,直到我们到了水上市场,看到一条瘸腿的流浪狗坐在花坛中,我们想把吃剩的玉米棒给它,才发现它很可爱,因为——就连墨西哥的狗眼睛都很大!
4 美丽的遗憾
现在才发现,之前在日本和夏威夷一个人呆着的时候,都文思枯竭,甚至有些Literally说不出话来。在日本问题倒不大,因为日本不管是人文书报、在街上的食物和人甚至标语,还是自然风光,都是一等一的审美。富士山脚下的日出和星星、在东京最后两天骤然飘起的大雪和意料之外的樱花……遍地都是感官上的愉悦刺激,和内心的情绪来回压制度过那五天。到了夏威夷的时候,发现这样下去不行,便有一天关了手机到一个远一些的海边,任由这浪潮一起一落。潮起时,我的脚被冰凉的海水浸没,陷进流水带来的沙子里;潮落时,脚丫子又暴露在阳光之下,上面什么遮挡都没有了。偶尔来一个大浪,把裤腿都沾湿了,我打个趔趄,过了几秒浪也褪去了。就这样一下午,我一边沿着海滩走着,一边用英文和自己自言自语,说着这几天解不开的心结。说了一会儿,我坐下,打开日记本开始写。写不明白了,我又回到海水里。直到天黑风起,我突然明白了,Emotions are like tides, we don’t fight against it, we just take a chair and observe it. 这句话其实是我在2022年的时候,在肯尼亚实习,第一次坐在Yi的车上,我鼓起勇气问了她一个问题:“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吗?” 现在想来这个问题是多么的“愚蠢”,哈哈!但当时她并没有嘲笑我,而是解释给我听,她很喜欢的一个歌手曾经在节目上分享过如此比喻,情绪就像潮水,会起会落,我们能做的只有搬一把椅子坐在那里。
那个夏天我还没有开始我的佛学心理咨询硕士,直到去年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才真正深刻地感受、练习,也明白了,原来这就是“正念”啊!我记得那个夏天在肯尼亚实习完,我和同期实习生一起去了旁边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其中有一天我坐在东印度洋的海边一整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太阳是会从头顶有轨迹地落下,原来一天会有两次涨潮两次退潮(因为涨潮的时候几乎要打到我们的沙滩椅),也是那一天,我突然被大自然上了这样的一课:我第一次明白,不论我们的心情是喜是忧,太阳和月亮总会按时起,按时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原来下雨的时候如果没伞,就找个地方躲一躲,实在不行就在雨里淋着,雨总会过去的,(也许是海岛特色雨,在其他地方就说不定了),天总会黑也总会亮的。好像每当我想到这些时候,我就觉得,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夏威夷扯远了。总之,在夏威夷的倒数第二天,我坐在沙滩上又发呆了一整天,拿出Y送给我的《正念是一朵花》,读了几章之后突然读到有一章里写一位印度瑜伽大师在夏威夷海滩冲浪,告诉大家“你无法遏制波涛,但你可以学会冲浪”,我看着夏威夷的日落和冲浪的人们,觉得是缘分的安排。只可惜我的正念修习可能还是不够,没有让我强大到可以自如地应对情绪。所以直到到了墨西哥城和朋友们见上面说上话,我好像才时而觉得好了些。唉!
说回“美丽的遗憾”,其实也是我想写这篇文章的一个最开始想分享的故事。我们在墨西哥城第二晚搬到了reforma区的一个酒店,从在酒店的对街下车开始,就有一位男人主动过来热情地来为我们提行李。我第一反应并不能确定他是否是酒店的工作人员,毕竟我们订的也不是什么高级的豪华酒店,他也没穿制服,通常工作人员也不会特意过马路来帮忙拿——他怎么就知道我们一定是这家酒店的客人?如果我们已经走到酒店门口了,帮我们拿一下倒也正常。
而我一方面是因为警觉,不知道这男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大概率是想要小费,而我们一来自己也拿得动,二来也没有足够的现金,三来也不知道该给多少(没错,我的脑子就是可以一瞬间转出这么多信息)——综上所述,我决定试图从他手里抢回行李自己拿。
在前台办完入住,他又主动过来帮我们把行李抬上几级台阶到电梯口,我们只能和他说muchas gracias(西班牙语:非常感谢),便在他的鞠躬和笑脸致意下关上电梯门。“他看上去不像坏人,大概是想要小费吧”,我用中文和Arena说。
后来下午出去的时候,我们一边在大堂等车,Arena一边用西语和他攀谈。最开始我们以为一辆红车是我们的,他便上前准备帮我们打开车门,结果发现不是。过了半分钟,红车真正的乘客从对面的银行过来了,他边和我们聊天边上前帮那位女士开门,看到这里我便费解了、同样的疑惑又出现了——他图啥?(就像我对那位在民宿门口吹萨克斯的人的疑问一样)。因为这位女士甚至不是这个酒店的客人,也没有给他小费,只是道谢。
第二天中午准备退房的时候,我们商量着,如果到时候他还在的话,我们就把仅有的零钱给他作为小费吧。可他一开始并没有出现。后来Arena忙着打车,这哥们估计是吃完饭回来了,他便站在酒店的门口,几乎是贴着墙站着,我通过玻璃的反射看到他带着挺拔鼻子的侧脸,以及大大的眼睛,似乎有目的、又似乎没有目的地看着周围的街。那却是一种很真诚的眼神,好像里面并没有隐藏着什么黯淡或苦难,相反似乎是充满希望的,又像是平静的。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位背着黑色垃圾袋的老爷爷,他便小跑上前接过垃圾袋,又接过老爷爷给他的几个硬币,便往街的前进方向跑去了。
在这一刻,我明白了,他大概是个在这街区“找点忙来帮”,有些他帮助的人会给他点小费。我从没想过这也能是个“工作”。我的本性不改,一下子又开始思考,他这样一天能赚多少钱呢?他大概有房子吧,只需要赚点钱够吃塔可吧!他有孩子要养吗?有家庭吗?他似乎穿着挺体面……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同时,我也在担心,他会去多久呢?眼看着我们打的车快到了,万一我们出发了他还没回来,我们连给他小费、知道他名字的机会都没有。
就在这样飞速运转的同时,Arena和我说,车到了。我把东西挪到车上,一边遗憾着这一次他没来帮忙,不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他小费;直到坐进车里,准备启程的时候,我突然透过前挡风玻璃看见一个穿白色衬衫的身影向我们这个方向小跑来,越来越近——太好了,是他!
Arena摇下车窗,他似乎也刚好才认出了我们,又露出他的招牌笑容,向我们挥手,另一只手里还拿着空的黑色垃圾袋。可在这一刻,司机一脚油门,他的脸瞬间移动到后面去。我之前的那么多内心活动自然还来不及和Arena说,只剩一句——“我们还没来得及给他小费!”
Arena一直主动承担了打车、沟通、付钱、翻译的角色,这已经让我很不好意思了,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再拜托她帮忙和司机说停一停车,我想把小费给到那个人手里(况且现金还在Arena手上)。我看着车窗外的红绿灯,驶过几个街口,才开口和Arena说:
这好像一个美丽的遗憾啊。
写到这里,我问自己,在遗憾些什么呢?
我想,是一些未能解答的好奇的遗憾,一些对没能给善良的人一些无关痛痒的报酬的遗憾,我本该至少知道他的名字的,或者和他合个照。
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其实我若是要找,应该是可以再次找到他的。本想着第二天回墨西哥城的时候再来弥补这个美丽的遗憾,可直到汽车出了墨西哥城,路过了机场,我便知道第二天我应该是会直接从Puebla去机场的。
他便成为一个美丽的遗憾了。
5 沙龙?
也许从墨西哥开始,是我近几年来第一次重新学会“用眼睛去记住”一些瞬间。可有意思的是,当时K“用眼睛去记住”、我用拍视频去记住的时刻,车里正在播放的是陈奕迅的《沙龙》,当时我们只是都觉得很好听。我后来查了这首歌词的意思是,用照片可以留住那些有温度、速度、温柔或愤怒的时刻,那些港湾晚灯、山顶破晓、升职那刻、新婚那朝的一秒,“要拍照的事可不少”——原来沙龙是那种摄影工作室的意思。也许过几年我再回到墨西哥城,那人还在或是不在了。又也许,我明天还是请Arena帮我回到那酒店门口一次,去找那人,也许等不到他,又也许Arena帮我问完想问他的问题之后,发现他只是个贪财的普通人,甚至有可能是个谋财害命的人,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高尚。都有可能。
整个飞机的人几乎都在睡觉,只有我还不知道在哪个时区亢奋得很,不过写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回想起来墨西哥人好像真的没什么班味儿(也许有班味儿的还在写字楼里),有很多“街溜子”,就算是有天我们挡到了一位穿西装皮鞋的人的路,对方也只是和我们笑笑,继续往前走着。
在Puebla的时候大家就那样坐在街边的长椅上,看书、听音乐、聊天、接吻……Arena说很像西班牙,像她去交换的时候那些文学院的同学,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其中有一个说自己毕业之后的计划就是去当咖啡师。我没去过西班牙,但那一刻我走在街上,看着又一位没见过的街头音乐家,我和Arena说,我其中一个人生梦想就是在街头弹琴唱歌(另外两个分别是做南极探险队员、去田野和前线)。
其实我几乎不会放过我看到的每一架能弹的钢琴,也几乎不会错过每一次能唱歌的机会。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一家餐吧,正式营业时间结束后我们便会拉上帘子,大家一起喝酒弹琴唱歌才刚刚开始,那时候我会拍视频记录,一方面是这样的盛宴在当时太难得珍贵,另一方面也有日后说不定要拿出来吹嘘或回味的特殊原因在。2020年的冬天,S来宁波找我,我们在三江口散步,看到有点歌唱歌的,我和S站在桥洞底下纠结良久,最终决定要唱后,S果断帮我扫了20块钱,我估计唱的又是《一千年以后》吧。那是我继小学二年级没拿到十佳小歌星、初二没过十佳歌手初赛、高二在全校决赛跑调丢人到第二天都不想来上学、大二又参加线上Singing Contest自以为稳过结果收获了一个极低评分之后,终于又在公开场合唱了一次歌。其实我在研二的时候又腆着脸报名了一次本科生的歌唱比赛,但这次我连初赛都没去参加。除非我再读一次书,不然我好像这辈子都无法弥补这个遗憾了。也许我唱的是真的不好,一紧张更唱不好。
这趟旅行刚开始,到新加坡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金沙散步,听到一个印尼双人组合在弹吉它唱歌,我停了下来,在《Everything Has Changed》的时候落泪了。这是我第一次不想在那些触动到我的时刻录影,我想静静地感受,“用眼睛去记住”,可我最后还是在最后一遍副歌的时候擦掉眼泪拿出了手机。又过了几首歌,我走上前,问他们我可不可以点歌来唱,我点了《All Too Well》,似乎又是唱得没那么好,也没有什么路人为我鼓掌或停留。但这好像不重要了,比较重要的是,这次没有人帮我录影,乐队小姐姐的手机架在那里,但我最终也没有在IG上问他们要视频。在新加坡还参与了《基本无害》的线下录制,结尾唱歌环节时候我自告奋勇带头唱了《一千年以后》,好像这次总算还唱得不错。
也有好几次和S散步的时候,我遇到公共的钢琴都会上去弹一两首,S总是会拿起手机在我背后悄悄录视频,然后我又会尴尬地说“别录了”。原来大多数人总是会倾向于拿起手机记录罕有的时刻,可似乎真的是当我们不再依赖科技帮我们记住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才会更加努力地感受当下;也有可能是因为相信“以后还会有”,所以这一次可以先用大脑记录,等到哪天真的变成最后一次了,再“留个底”也不迟。
应该是的。墨西哥的机场没有出境海关,却有共享钢琴,也许在这里音乐真的永远都会有“下一次”,所以可以不用担忧地享受这一次。
而墨西哥不仅教会我,弹琴和唱歌的时候不一定需要一个手机支架录影,还教会我的是,不一定需要观众和掌声,甚至不一定需要一个听上去“合理”的目的。只需要我想弹、想唱,这就是原因,这就是目的,合理到不能再合理,充分到不能再充分。早上我还鼓起勇气把之前在新加坡录的那期自己的播客,分享到了那个线下录制六七十人的大群,我告诉自己,就算没有人回应,顶多是有些尴尬而已,我只要分享了,哪怕有一个人听了,哪怕没人听,都可以。
在墨西哥城那个酒店的门口,我还看到擦鞋匠,一位女士穿着裙子抬起脚上的菲拉格慕皮鞋,擦鞋匠一边和她聊天一边擦着,和《寻梦环游记》里的场景还真差不多,这里的人也还真像电影里那样热爱音乐、我甚至在Puebla的餐馆里听到了我应该是人生中听的第一首西班牙语歌《La Rosa》,店里的阿姨在音响喇叭下切着青椒丝儿。我想拍但没有拍,昨晚那群青年在窗外唱歌的时候我也没有拍。
出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在设想每个目的地我应该有怎样的产出,试图找出一个模板答案。我要写文章、拍照、发攻略、录播客,做一全套。
而也许是在日本和夏威夷的失语,也许是拉美的松弛,我已经接受了我只能随缘尽量产出的事实。我太想抓住每一个瞬间了,可殊不知文字永远只能记录当下。我又担心各个平台和文风不一样,也无法展现我“完整的旅途”;后来发现我就应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毕竟在互联网上或是旁人的印象中,再怎么拼凑,也不可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我”。
出发前我一直纠结的是,这趟拉美旅行玩不够,要不是已经计划好了四月份在美国的路线,我本应多留一些时间趁年轻把中南美走个遍的,毕竟这么远。来墨西哥和大家汇合后我才发现,也许有时候旅途中同行的人才是更重要的。我有时候会口误把墨西哥说成智利或者西班牙,就像卖咖啡的人把Arena的名字也拼错。每次别人问我们叫什么,Arena总是会说,“我叫Arena,她叫Lumi”,即使我通常只会死死守住我的“Hola”“Gracias”“Amiga”三件套在旁边傻傻得笑,或者最多在被称作“Senora”或者“Senorita”的时候欣喜不已;而不知怎么的,墨西哥人好像总是对我的名字更有反应,可明明Arena在西班牙语里是有实际含义的(沙)。每次她用西班牙语和别人交谈,我总是有一种莫名地为她感到高兴,当然也有一部分为自己感到幸运吧,因为我知道我只要这样静静地张大眼睛看着她们,Arena自会在谈到精彩的时刻用中文转述给我,太幸福了!
等我下次来当南极探险队员了,或者西班牙语精进一点了,不管是墨西哥还是拉美/南美其他国家,我都还会再来的,墨西哥的物价和天气也很适合数字游民。反正在香港上班的时候也是入不敷出,不如出来吹吹拉美松弛自由的风吧!在高速上看着两边盛开的蓝花楹和帽子树却来不及拍照的时候,我心想,希望以后的伤感是因为错过一些花、错过一些善意、错过一些音乐,而不要再为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人为事物纠结或者想要改变。
但其实花、善意和音乐我又可曾真正错过?只是我的相机错过了。
附:一些墨西哥旅行中 相机没错过的画面


水上市场

眼睛很大的流浪狗(眼睛真的很大)但它脚有点瘸了呜呜呜

好吃的墨西哥三明治&taco!



花开啦


松鼠和老鼠都是鼠



soumaya美术馆,是当地一个很有钱的人斥巨资建的,里面有各种藏品,他希望给墨西哥的青年人提供更多的艺术教育。里面有爱迪生的留声机!

在美术馆外面和当地保安一起打了会乒乓球,好搞笑

据说墨西哥的可乐是最好喝的,因为是用蔗糖。可惜我没喝!


这个taco太好吃了!人均一百多人民币吃到撑,推荐推荐!

墨西哥人真的随时随地吃肉,好开心


擦鞋匠

擦车匠(但他没有拿到钱!)

在普埃布拉拉小提琴的人

人手一根玉米

站在房顶上的狗



山顶日落和月亮,这是一座活火山




一些戳到我的涂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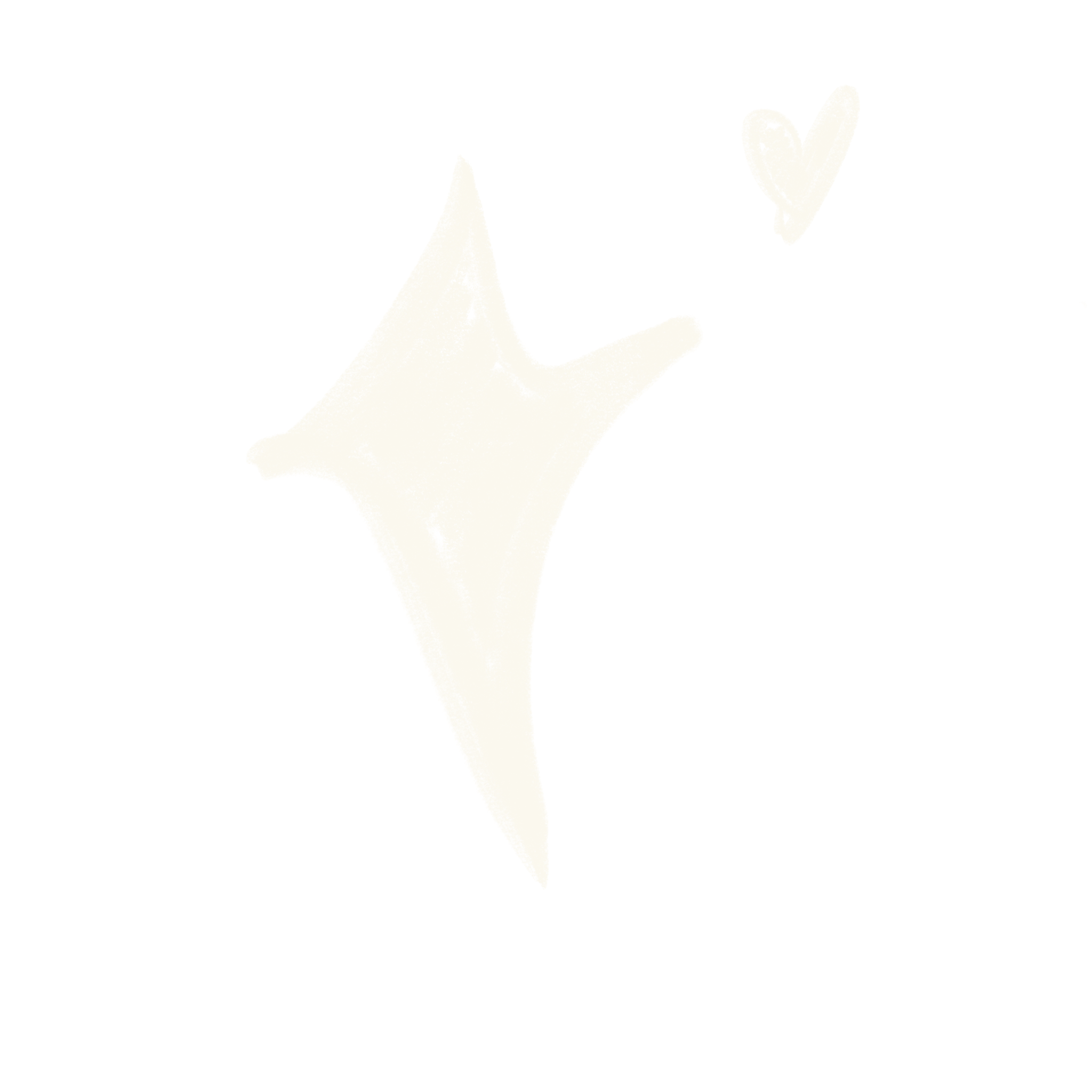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