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不想做孩子和花
上个秋天在宁波的时候曾经和K讨论,我说下辈子我不想当人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开车,看到高架路边花坛里的花,我看了好几眼,还是觉得各色的花瓣太娇嫩,在那秋风中好像吹几天便会留下折痕或是枯萎,当时的我不太能接受,我便想了想,说,我下辈子想做路边一颗草。
果不其然,K问我,为什么不想做一朵花。
我在心里想着,草好啊,看上去不怕风吹雨淋的,受了伤也看不出来。
花,给我一种凋零了就是结束了的感觉,来年春天开的新的花便不再是“自己”了。而每一颗草似乎并没有太多不同,所以好像到了“春风吹又生”的时候,又可以继续存在着。
写到这里,我在想,这是一种对于长生和永恒的追求吗?冬天的时候草最多只是休眠,但似乎还是可以静静地在路边观察着。冬去春来四季轮回,好像年复一年也不用有太多对于凋零的顾虑。可学过佛学的我应该知道,追求永恒,也就是追求无常的“常”,是愚蠢的。
有天我和K一起吃饭,他说要到隔壁买杯咖啡,让我在小程序上选。当时的我控糖还比较严格,而特调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果汁和糖在里面,我对着十几杯里每一杯的配料表似乎都没有完全满意的,但看到有一杯的名字叫做“我想做孩子和花”。虽然我并不想做孩子,也并不想做花,但我和K一致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便自作主张帮我点了。吃完饭我拿着那杯饮料在月湖公园闲逛,看着这个名字,想到如果要做孩子的话,我又得把以前那些写作业、应付考试、守规矩的生活再来一遍,感觉是万万不想再经历一遍的。
从小到大我的成长轨迹算是非常幸运,不知怎么的就成为了所谓的好学生,也许是因为从外婆那里继承了一些奋斗和争强好胜的基因,我总是习惯性地想把题目都做出来,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在社交和对外表现上让大家都喜欢我……
我知道这背后也包含着无数的运气、个人的努力、家庭的托举……
再来一遍的话,我完全不能保证自己能足够幸运到拥有和现在可以比肩的“结局”。
于是我想做一棵草。
2 气球
在秘鲁的时候,坐在第一排司机和导游的中间,我看到眼前有很多盛开在高原的花,它们长得好像就和平原上不太一样,很有那种恣意生长得野生的感觉,我当时想着说,要是来生在这里做一朵花也不错,每天看看低低的云、傻乎乎的羊驼、和一群高原反应还要强撑着来这里的人。
后来到了智利,到了几乎是地球最南端的百内国家公园。我的智利之行是没有游记的。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是不是醉氧了,又或者是身体上实在太累了,现在想来那几天好像一场幻梦,以至于在离开智利的那晚,在机场正对面的酒店大堂里,我心想着,不如就在这个盛产葡萄酒的国家破罐子破摔,便点了一杯酒单上最贵的希拉红酒,不过十美金——我要一梦到底、一醉方休!
几口红酒下肚之后真的心情都变化了些,我开始回复几天没回的那些消息、和美西美东加拿大的朋友们一一道歉取消行程、向前几天在我低迷的时候拉我一把的朋友们表示感谢、甚至还能有气力向大家表达祝福了。真是神奇!其实我至今也没明白这趟南美之行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太累了,还是缺少独处的时间了,还是因为西语不熟悉了,还是因为离家太远了,还是因为智利之行太过于偏重自然、于我而言缺少了人文和信息的摄入……我真的想不明白。罢了罢了,也许旅行真的不在目的地和风景本身,而在于某些瞬间吧。
在老挝的时候,那个瞬间应该是我和小花坐在早市的咖啡馆里看到一个女人拎起一条鲶鱼的那一个瞬间,我说“这才是我”、“这才是旅行的意义”;而从复活节岛开始,身体休息过来一些之后,我也一直在思考旅行的意义。也许是在离开南美前微醺的那个瞬间,我回到了曾经那个可以向身边的人输出情绪价值和各种价值的我自己,那也是现阶段的我所定义的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我从一种消耗的过程中回来了,所以我重新快乐了。
其实我一直在愁,智利的游记到底要怎么写。直到刚才上了飞机,打开三毛的中美洲纪行,发现她其实也只是在描述一些旅途中的心路想法,并非局限于风景,我才突然感悟。毕竟我写东西也没人给我布置任务,也没人给我稿费,纯粹就是一种自己的输出和留纪念,我又何必把自己框的太死!智利的风景都在照片里了(不知道有没有留在心里),不如就写写现在的内心所想,有人看或无人看都没有所谓。
3 消耗
在智利我突然明白,其实旅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耗。
一是对于体力的消耗,护照夹里已经存了将近二十张机票,这么大的南美大陆我又把自己折腾到了最南端,回想起来总是有一些在往返机场路上的片段——不累才怪!我似乎也已经不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那个时候的体力和年纪了。在路上碰到很多五六十岁老年团,大多是来自北京上海,偶然遇到一个来自昆明的团(也许这些城市的老年人都想的比较明白,其他城市的老年人们大概基本都在帮忙带孙子吧!)
他们基本都是拉美四五十天,十个人互相照应,每到一个国家就有地陪举着牌子包车接送安排景点,住的也基本都是比较高档的地方,也许这样的话还行。不过少年有少年游,到了老了又有不同的玩法和不同的感慨。倘若旅行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每个地点其实都只是记忆的一种发生地和载体。
二是对于脑力的消耗,从明天早上几点起床、中午吃什么、到大行程的安排,中间涉及大量的决策。而决策本身就是一件很消耗的事情。这趟旅行其实我已经尽量减少了很多决策,比如只穿白色的衣服便减少了色彩搭配的决策、只背一个背包就不必再纠结是否要买某些纪念品,等等。
三是对于金钱的消耗,跑的那么远,花那么多钱,坐那么久的飞机,一直挥霍金钱总归有些良心不安,钱花下去了,人总是会期待更多的收获的。
而我认为我还是需要从一部分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价值创造感的那类人。
旅行可以给我带来解决问题后带来的成就感,在旅途中收获新的对话和友谊以及输出带来的成就感,以及,其实走这么远本身就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也许下次计划旅行之前,我会重新考虑各方面消耗和获得成就感的cost and benefit(老中商科学生附体),再做决定吧!
4 一朵云
回国之后在浦东,N的家里,我们聊到下辈子并不想再做人。
我说,我想做一棵草
她说,我想做一朵云
我根本不想再做有感情有生命的东西
我就想做一朵云
云是自由的,还可以化成雨,可以循环,
云是自由的。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云是自由的。
云本质上是水,
and we’re all water.
而我住的城市没有春天。
5 地球表面
自从坐上飞往纳塔莱斯小镇的飞机开始,我就有一种好像在做梦的感觉。飞机沿着安第斯山脉一路向南,一路都是太丰饶的地貌,加上晴朗天气带来的无敌能见度,仿佛在看地理纪录片。在整个三小时的飞行中,所有人的脑袋基本都长在左右的窗玻璃上,透过座位和窗户的缝隙可以看到一整排都是各种颜色的头发和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坐在靠过道的旅客们则因为看不到窗外的景色而焦急不已,不断地伸长脖子和举着手机的手臂,想要拍摄一些窗外的美景。
这班航班就是这样神奇且特别的,几乎每位坐在这里的旅客都只有一个目的——去位于南纬五十度的百内国家公园,吹吹世界尽头的西风,去徒步、看山、探险。
刚走下飞机的时候,我的心情并不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感到新奇,而是一种熟悉和遗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三年底的时候,我曾经去到另一个世界尽头的小镇,阿根廷的乌斯怀亚,从那里登船前往南极。我记得那天我低估了世界尽头的温度,穿着短裙降落在了七摄氏度的世界最南端城市,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纬度的植被,它们是“恣意生长”四个字的具象化。
从南极回来之后,我许下一个愿望,我想要做南极探险队员。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2027年来做这个。而第二年(2024年),我便考出了所需的全部证书,如愿拿到了offer,却因为没有忠于自己的内心所想而和它失之交臂了。
而现在,我知道我又将回去。我很愉快。
我也再也不会错过我想做的事情了。
6 撤离
今天是公元2025年的3月25号,是我在这座岛上存在的第三十六万三千二百八十四天。我在这座被称作“复活节岛”的岛屿北角,和身边的十四个伙伴一起,那些被称为“人类”的人叫我们摩艾,意思是石像。整座岛上大概有一千多个和我们差不多的摩艾,但数我们十五个最有名。我们站在海边,每天都会有一群一群的人类专门来看我们,拿出那个叫手机的东西和我们拍照,还会专门绕到我们的背后,然后他们就会发现只有我的背面有一个屁股沟,他们会大笑,拍照,然后离开。
今天来了一个穿着全白衣服的女孩,她看上去并不快乐。她在这座岛上,打电话、偶尔哭泣、经常饿肚子。她买了六盒牛奶,她在为没有打翻的牛奶哭泣。后来,她的朋友劝她回家,她也觉得是时候回家了。她看机票,她几乎没网。她高兴地想哭,她为自己终于感到伤心而快乐。
走之前的那天下午,她一个人站在海岸边,站在海浪反复进退的边缘。
她知道下次再来看这太平洋正中心的大海将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于是她舍不得离开。
突然一个大浪打来,把她的鞋子袜子裤子都打湿了。她这才决定站起来,踩着一鞋底的水,再回望几眼,看看表,终于下定决心离开。
.
她来看摩艾。她来看我。
而下个星期开始,我将不会在这里。
后记:听说她总是这样,一定要浑身湿透了才肯离开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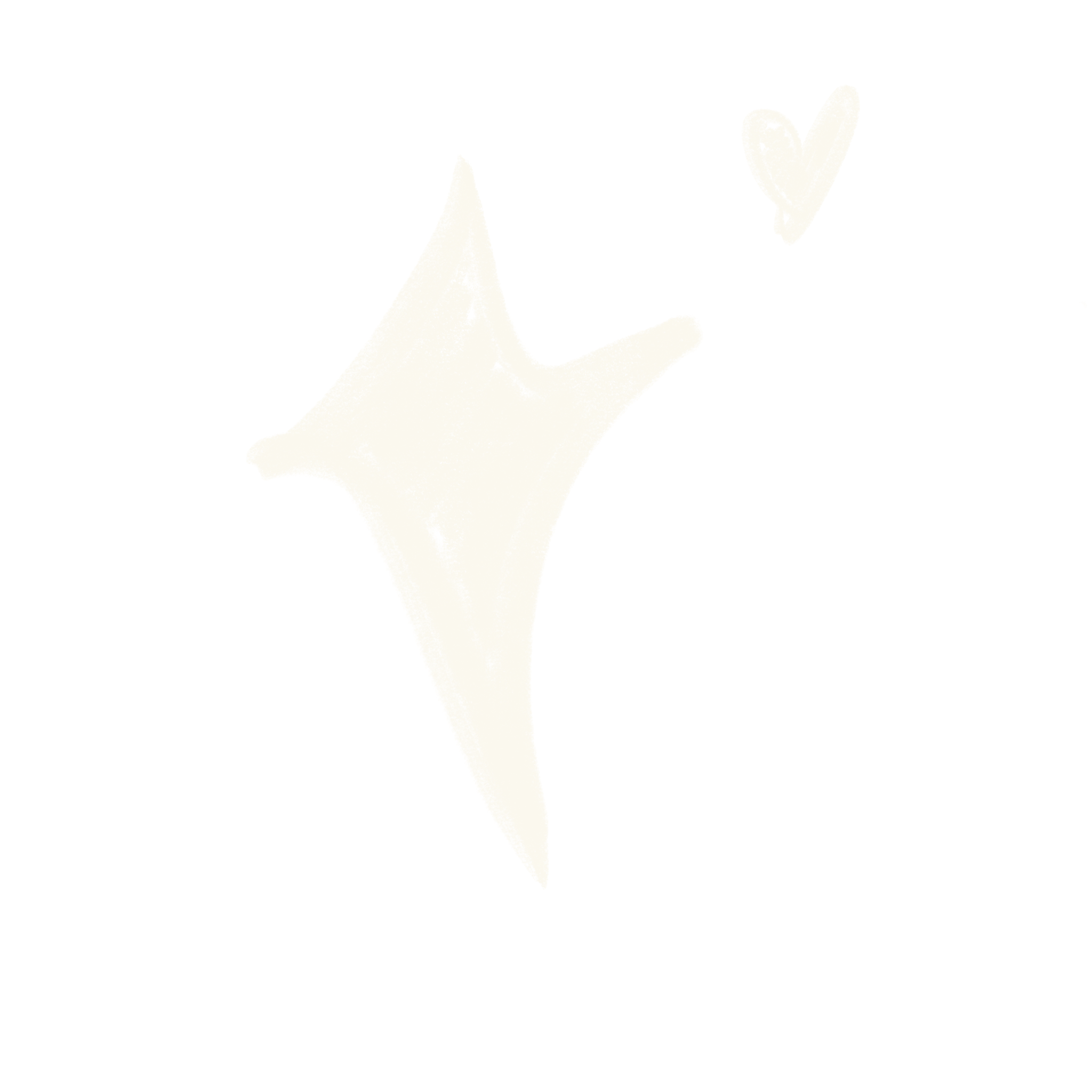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